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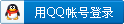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西阴遗址位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部一高地,俗称“灰土岭”的地方,北倚鸣条岗,南临青龙河,西南距战国时期的古魏国都城“安邑”即“禹王城”8公里,东北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下冯遗址”8公里。遗址范围:南至西阴村南今“嫘祖庙”一带,北至“灰土岭”边缘,东至村东一条南北向小路;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东南部被西阴村形成半环状包围和破坏。1926年,由李济和袁复礼先生调查发现并首次发掘。1994年10月1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1996年11月20日,西阴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经夏县西阴村时,李济先生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 不久,他们即返回北京。嗣后,李济因病耽搁了半年时间,当他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即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先生商量发掘西阴遗址这件事。毕士博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商量了几条合作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由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承担;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待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 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米×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为1.17米—1.25米。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得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先生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现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得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卫 斯/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