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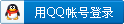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在《倦怠社会》一书中,韩炳哲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社会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在其中占据主导的是各种否定性的禁令。与规训社会相反,功绩社会越来越摆脱了否定性,“不断升级的去管制化进程取消了否定性”。规训社会的情态动词是“不允许”和“应当”,而功绩社会的情态动词则是一种积极的、能够打破界限的“能够”,或者是集体符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们可以办到!”。
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的范式转化是实现生产最大化的“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规训社会的禁令规训法则对于社会生产的作用便达到了极限,妨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的转化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肯定性的“能够”比否定性的“应当”更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当然,从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规训的消失,功绩的主体依然接受社会的规训,但是他超越了规训法则。
规训社会的否定性,制造出来的“疯人和罪犯”;而功绩社会的肯定性生产出的则是“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对于现代抑郁症泛滥的现象,阿兰·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等学者完全从心理的层面来分析,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他们将抑郁症的起因,归因于个体摆脱规训社会的禁令之后所拥有的过度的自主性和所承担的过度的责任:“当控制行为的规训模式让位于另一种规范时,换言之,过去通过权威和禁令分给社会阶级和两性角色,如今每个人必须自发地行动,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症就在这时开始流行……抑郁症患者没有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他在必须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尽。”而在韩炳哲看来,埃亨伯格等人注意到了功绩主体患有心理疾病,但却没有发现这种心理疾病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关系。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统治关系造成了一种基于自我剥削机制的“绩效命令”,并引发了抑郁症等现代精神疾病:“并非过度的责任和自主性导致疾病,而是作为晚期现代社会新戒律的绩效命令(Imperativ der Leistung)”。
在功绩社会中,人们不再受到外在的统治机构的控制,也不再屈从于任何个人,成为了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这种脱离他者的自由却并没有给主体带来释放和解脱,而是形成了一种“强制的自由”:“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绩效主体成为了自身的雇主,通过对自我的剥削以达到绩效最大化的目标。这种自我剥削甚至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因此,韩炳哲将功绩社会的人类称为只会劳作的“末人”。他们在没有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完全自愿地剥削自我。抑郁症等功绩社会的精神疾病,就是这种悖论性自由在病理学上的体现。绩效强迫症促使他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效能,他同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当功绩主体不能够继续工作时,抑郁症就会爆发,“它首先是一种对工作、‘能够’的倦怠感”。
抑郁症等现代心理疾病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压抑和否定机制造成的,也不是个人与他者之间矛盾的内化。相反,现代功绩主体患病的原因并不在于他者层面,而是“过度紧张的、过量的、自恋式的自我指涉”。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并在同自身的斗争中困苦不堪:“他将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之中。”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成为了21世纪的流行病:“它们都带有自我攻击的特征。病人对自身施加暴力、剥削自我。自我形成的暴力取代了他者的暴力,前者的破坏力更大,由于受害者生活在一中虚假的自由感之中。”
除了过量的自我剥削之外,与他人之间连接的消失也是现代抑郁症产生的重要原因:“新媒体和信息交流技术也逐渐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关联。”韩炳哲指出:“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拥有过量的选择,因此没有能力建立一种密切的连接。”现代晚期的自我将大部分的“力比多”能量投注到自身身上,而剩余的力比多则被分配到“不断增多的交流和短暂、肤浅的关系之中。这种关联是薄弱的,因此很容易把力比多从一个对象转移至新的对象。”当然,个体在社交网络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朋友”,但这些“朋友”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在于:“提升个体的自恋式自我感受。他们构成了一群鼓掌喝彩的观众,为自我提供关注,而自我则如同商品一样展示自身。”因此,现代功绩主体的抑郁症完全不同于“悲伤”,因为“悲伤”意味着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力比多关联,而丧失了与他者连接的现代功绩主体已经丧失了“悲伤”的能力。在抑郁症患者身上,“一切关联被解除,包括同自身的联系。”
韩炳哲进一步将功绩社会中的功绩主体与阿甘本所说的“神圣人”联系起来。阿甘本所说的神圣人是一种绝对可以被杀死的生命,是一种被现代社会和政治共同体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群,包括集中营中的犹太人、欧洲难民营中的难民、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和恐怖分子、美国黑人社区的黑人等等。而韩炳哲看来,现代功绩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神圣人”。但是这种“现代晚期的神圣人”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他们不是绝对可以被杀死的对象,而是绝对无法被杀的对象,但是他们的生命如同“僵尸”一般:“他过度活跃,以至于他既不能死去,也毫无生气”。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功绩社会中这些身患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的人群所显示出的症状,与集中营中的囚犯高度相似:“这些筋疲力尽、困倦不堪的囚犯,如同身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变得极度麻木、冷漠,甚至无法分辨躯体的寒冷和看守的指令。”生活在现代功绩社会的个体虽然看起来拥有充分的自由,但又仿佛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无法挣脱的囚笼中。
赵丁琪 · 2024-10-06 · 来源:读书札记与学术译介|微信公众号
标题 : 自我剥削、功绩社会与现代人的精神疾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