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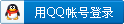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母亲的夜色
□王文平
母亲的脸上,总是溢满了柔和的笑意。
每当溜进被窝闭上眼睛时,我的耳里便会响起纺线车嗡嗡的声音。我喜欢在夜里聆听母亲哼唱的蒲剧掺和着纺车发出的嗡嗡声,有如天籁。看着软绵绵的棉花伴随着母亲圆润的嗓音,从手里婉转成细细的棉线,觉得实在神奇。纺车的嗡嗡声,就是我幼年的催眠曲。
织棉布、纳鞋底,做棉衣裤、棉鞋,剪窗花,裱天花板……母亲总是晚上做这些活儿。纳鞋底也是功夫活儿,如豆的油灯,橘黄色的火苗外裹着一层淡淡的红晕。母亲左手食指上带着顶针,右手大号针在头发里一抿,只听得“哧啦”一声,针尖穿过厚厚的千层底。她拿过小钳子,夹住针头,猛地向上一拔,随着手臂举起收回,长长的线绳便换了两下。她一手压住鞋底,把线绳使劲吃紧,厚厚的千层底上密密麻麻印下均匀整齐的小坑。鞋底上针眼数不清,就像母亲走过的坑坑洼洼的岁月。而日久天长印刻的母亲皲裂的手纹,我同样数不清……
我们家的天花板每年都要重新糊一遍报纸,这都归功于老鼠。每到夜晚,黑咕隆咚的天花板上,星点儿的糨糊成了老鼠啃食磨牙的消闲。不知道是忙还是别的原因,父亲从来没有裱糊过天花板,大概是不会吧,但母亲却是这方面的强手。
裱天花板那晚,母亲会提前熬好糨糊,父亲从学校拿回些旧报纸,搭好架子,我和哥哥把报纸整齐地摆在桌子上,用玉米叶绑成刷子,在报纸上均匀地涂上糨糊,踮着脚递给母亲。架子上的母亲拿着小笤帚举着报纸,先对齐一个边,看准了,用小笤帚嗖地一刷,报纸便整整齐齐地贴在天花板上。
或者是一种美好的愿想,每年母亲都要剪窗花、贴窗花。母亲的剪纸,可是十里八村的绝技,一盏煤油灯、一张大红纸、一支铅笔、一把小剪,便可以剪出十二生肖、福禄寿喜图等各色各样的图画。心灵手巧的母亲把红纸里面朝外,折成四层,在煤油灯上均匀地熏黑,用铅笔在熏黑的一面描出图形,拿着小剪刀,连剜带剪,不一会儿,红纸上的图案就像是从纸上跳了下来,飞到了纸糊的窗格子里。
晚上回来陪母亲唠嗑:“妈,现在社会好吧,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母亲看着我,又看了看窗外的夜色,笑着说:“这是我今天剪的窗花,好看吗?”
母亲说话的时候,脸上又漾着暖暖的笑意。
窗外,月朗星稀,夜色如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