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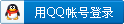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罐罐饭”的味道
□孙宏恩
午夜梦回,行走处还是那昔年旧景。矗立在校园中央的大戏台,因年久失修早已无人涉足,成行的泡桐树枝柯交错洒下一片阴凉。这就是我曾任教多年的一所乡村小学。
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用土墙隔成两个空间,宽大的一边是教室,窄而长的一边是我的卧室兼我和同事们的餐厅,房子的顶棚和土炕的周围都裱糊着一层旧报纸。时间久了,我能把报纸上的内容大段大段地背下来,甚至不用抬头就能猜出顶棚上哪个方位第几张报纸上的标题。那时候,背报纸、猜标题是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我以此为乐,乐此不疲。
住得简陋,生活单调,吃饭却从没有受过罪,因为我们吃的是“罐罐饭”。
提起“罐罐饭”,我还闹过笑话: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刚刚到岗一会儿,正在熟悉学生,扭头一瞥,发现一位老人站在门外,我忙下讲台出教室,老人神情恭敬地喊我一声:“师傅……”我有些受宠若惊正不知所措时,老人发问了:“敢问师傅,您的字是……”我报上姓名后,心里暗想,村里人还这么文绉绉的,我哪里有什么字啊?接着老人又问一句:“范嘉禾在哪儿?”我以为老人是来学校找他的孙子范嘉禾的,就很认真地看了一下手里的花名表,摇摇头说不在这里。
临到吃饭时,我才知道自己错了,原来,那老人家里管老师饭,他是来学校取回盛饭的器具俗称“饭家伙”的。对于乡村教师的这种就餐方式,我是初次接触,对“饭家伙”一词,也是第一次听说,我可真是孤陋寡闻。
“饭家伙”是由三个物件组成,放馍的竹笼,上下两层的木质食盒叫提盒,那是放菜品的,还有一个盛汤的搪瓷桶。据说那个搪瓷桶是村主任专门从外地买回来的,之前好多年都是用瓦罐盛汤的,“罐罐饭”由此得名。
那些年,庄户人日子清苦,一年四季都是粗盐淡饭。偶尔也有改善伙食的时候,那就是管匠人饭、管工作员饭、管学校老师饭的时候,再有就是过年待客的饭了。
管匠人的饭,那只是有修缮工程的家户的专享;“工作员”是村里人对下乡干部的尊称,能管上工作员饭的必定是村里人公认的巧妇,村里派饭时还有经济状况方面的考量,绝大多数家庭无缘打理此事;说到过年待客,饭食也没有一定之规,丰俭视自家的面瓮是否有物自便。唯有管学校老师饭这件事是家家户户都必须经营的,似乎大家都以此为荣,明里暗里还有些竞争。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主妇们也没有几个是专职做饭的。农忙时节,在田里在场院,从早到晚汗流浃背干不停;农闲时,洗浆补衲织布纺花不分昼夜忙忙碌碌。下厨做饭只是捎带,凉的变热,生的做熟,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就很不错了,谁会有过高的要求呢?有米无米还真是一个大问题,箪瓢屡空是农户生活的真实写照。
可一旦轮到管学校老师的饭,那就大不一样了,家家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搜罗一些好面(小麦粉),拿出藏了好久的一斤半斤清油,提前蒸好馍晾酥了稳妥收拾,以待管饭的大日子,到时候工序繁复的粗粮细作,花样翻新的菜蔬式样都极尽巧思。年轻的家长做饭缺乏经验,一般请奶奶主厨,没有奶奶的家里会请来姥姥,有的会左邻右舍拉几位帮手,还有的干脆劳动村里的大厨来助阵。快到饭点时,还会有未来几天要管饭的家里来人观摩咨询,这一顿饭只说花费的心思就够感人的了。费心费力不小,报酬却不高,一顿饭一毛钱。
我们吃饭多的时候三五人,少的时候就我一个人。虽然不是什么美味,可碟儿碗儿也得摆下一桌子,临了,给人放三五毛钱回去,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老校长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村民敬重我们文化人,咱们出的钱没办法跟这顿饭的价值对等,只能算是一点心意,除了教好学,这一毛钱是对学生家长的劳作表示尊重之情,这就是礼尚往来啊。”
记得是一个教师节,村主任来学校慰问教师,同时带来了一个消息:经村委会研究决定,以前教师吃饭付费的制度取消了。老校长以为这是吃白食,持反对意见。村主任的态度十分诚恳,也十分坚决。那时候,改革开放之风已吹到乡村,村里已经有些人开始经商,走上了农商互补的路子,一些人把粮田改为经济作物田,收入明显增加,还有人进城务工了,整个村子的经济状况悄然发生着变化。村委会的决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温饱问题解决了,管老师饭的时候,再也不必为食材发愁了。馍越蒸越白,菜越做越多。“四菜一汤”传说是县长下乡吃饭的标准,而我们常常超过这个标准。除了四菜一汤,饭桌上还常常有些亮点,比如一碟潼关酱菜、半碗白糖、几颗煮鸡蛋……吃得最多的是煎饼、饸饹和饺子。
“好吃不过饺子”,可我们最怕吃饺子,有时候能一连十来天都吃饺子,起初是在饺子馅里做文章,荤的素的各有特色,后来连饺子皮上都体现着匠心。做饭人彼此之间不再互相打听做什么,但都有各人的小九九,变换着花样要把这一顿饭做出自己最高的水平。“蒸着省,擀着戏(浪费的意思),煎饼、饸饹吃得卖了地”,老辈人留下的谚语,却反其道行之,买菜买贵的,做饭做费的,管老师饭不计较省了还是费了。
虽然是家常便饭,也有超群的技艺。“金丝面”就是其中的一道美餐。利落的面条,浇上金黄的南瓜卤,形美色美,最美的是在味道,这美味来自繁复的制作过程:蛋清和面,饧半小时面松软了,然后戗面,以至揉到面足够硬,再放到温热处饧,三饧三戗之后,面细而光,此时开擀手感要好很多,几乎不用面粉,就可以擀到薄如纸张,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劙面。
据说,当年在农忙食堂里,七八个人揉面擀面,就等一个劙面把式上手,只见面案上折叠得厚厚的面片上,摆放着长长的擀面杖,劙面把式来了,高挽袖子,左手推着擀面杖,右手提起菜刀,眼看着擀面杖一点点向后挪移,刀起刀落间,细如发丝的面条在案板上跃动,一走神,劙完了,再看时,已经是一把一把的面条摊在了竹箅上了。一把就是一人份的量。待水烧开了,下面、捞面、浇卤、上桌,整个过程顺畅自然,利落爽脆,让人不得不佩服高手在民间。面叫“一窝丝”,吃进嘴里,是脆生生的,卤是软绵绵的,口感妙不可言。
这哪里是做饭,分明就是绝活表演嘛。再看看搪瓷桶里那清凌凌的一根面也不剩的面汤,舀起来口服心服。每每这个时候,大家品评着,溢于言表的满是感激。老校长就催着大家去教室候课,总要叮咛一番:“年轻人不能只当教书匠,还要塑造灵魂,教育学生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村里人都想让孩子有出息,掏心掏肝地对咱们,咱们可不能辜负了大家啊!”
吃“罐罐饭”的日子在时间的远方已沉淀成记忆,受惠于乡亲们那么多年,我早已与那一方水土血脉相连,那个古风犹存的村落,连同那舌尖上挥之不去的味道,常常让我魂牵梦萦,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临猗县蔡高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