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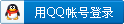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致村庄
作者:李卫红
这个村庄,是可以称之为祖籍的一个村落,一个位于北方的村落,也就是我的老家。
在汉语充满历史感和美学意境的阐述里,祖籍是有根的意义的,是一个可以溯源的载体,是在宗族先祖血亲的干流洄游而上,寻觅源头的第一驿站。
在壮阔无垠的黄土高原上,在奔涌千年的黄河边,在晋、陕交界处的那个隘口,有个叫禹门口的古渡口,不远处,有个叫北里的村子,我的祖籍就在那里。
黄河漂流到这里,经过上下几个起伏,变得渐次开阔起来,波浪开始和缓,开始不疾不徐。这是一段比较宽阔的河面,水流声渐轻,有了缓冲,黄河水特有的泥土气息开始弥漫,渐渐缭绕开来。
河边有纯正的黄河滩,淤泥是深黄色的,松软,润泽,日光照耀下泛起一圈圈亮光。轻轻走过去,再轻轻走回来,在河滩多走些,会慢慢感觉到和这条河亲近后的那种妥帖。离开河口,沿着河边往东,不多远处就到这个村庄了。
这个时候河岸两边总是安静的,甚少有人迹,这是一段适宜独自行走的河沿小径。走出十几里后,离河远一些了,就能影影绰绰看到一片乡土房屋的轮廓,应该就是这个村庄了。
快要靠近村边了,能看到村子的上方有缕缕白烟在飘浮着,这是一个有烟火气的地方。能看到村庄的几处边际,有一道道很深的沟壑,沟底长着成片成片的矮树,一簇簇的,从沟顶望去,像壮实茂密的灌木群,有风吹过,发出枝叶互相拍打的簌簌声响,像深夜里的黄河,波浪冲到河滩上又缓缓流走的声音……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是野枣树,老家的沟里长了很多很多的野枣树,长了好些年了,树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野枣。早年间,遇到饥荒的时候、吃不上饭的时候,这些野枣,是可以用来果腹的。
父亲是出生在这个村庄的,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和一支队伍一起离开了。父亲在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也很早去世了,然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村庄。
父亲是一名军人,很多回忆都是和战场、炮火、硝烟相连的。但是过了很多年,尤其是到了晚年,父亲会时常断断续续地回忆起那个村庄,那个老家,回忆起在老家短暂的童年。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又长又深的沟坎,那些弯弯曲曲、快要把村庄围拢起来的沟坎,和沟底下密密麻麻的野枣树。
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就背着筐,小心地爬到沟底,去捡拾那些成熟后掉落的野枣,把野枣蒸熟碾碎,掺在粗面里,一起蒸熟了吃。父亲在世的那些年里,即使是刚摘下来的新鲜枣子,他都会习惯地蒸熟了吃。他说过,从前靠着那些野枣,靠这吃法,多少年了,老家的村子里从来没有饿死过人。
我是在比父亲当年离开村庄略大一些的时候离开的,去了一个叫作城市的地方。其实我一直都是和父亲在一个城市生活,只是去了一个更大的城市,一个更遥远的城市。
那个城市名气很大,人也很多,终日都是熙熙攘攘的。我被夹裹在汹涌的人潮里,昼行夜伏,熙熙着去,攘攘地来。那里就像一个巨大的鼎,那里的气流时常裹挟起人流在波峰和谷底间上下疾速地翻腾、急剧地旋转。鼎的四周有横插斜穿的、犹如重金属粗横地相互摩擦、迸发出刺耳的异响,时刻在撕裂着耳膜。
那里没有高原、大河,那里没有蜿蜒、深邃的沟壑,那里没有四野的宁静,没有日光下从山涧吹来的柔暖和煦的风,那里从来没有长过野枣树……
在那里,我不知来时的路。
那里有很多人,和我有几近相似的过往,都有一个坐落在村庄的老家,但从未走进过这个地方。甚至在年少的时候,羞怯这个村庄与自己生命和身份的关联,一度想抹掉这种关联,一度在努力着,一步步走得越来越远。
直到某一天,已至中年,在那个喧嚣的城市过活很久了,浮沉中的凌乱和荒芜越来越像一堆堆杂草,渐渐地,那个曾经远远地搁置在一隅的村庄,那个叫作老家的地方,那越来越清晰的“根”的唤醒,越来越近的族亲和那不可逆的血亲浸染,就这样难以阻挡地涌来了……
就像夜下的黄河,河水缓缓地、一波一波地冲拂着河滩,一次又一次地冲拂着。
就这样,我踏上了寻觅这个村庄的路,我想来看看你,我已经到了来看你的年龄了。我沿着河边的小路走到了你的村口,我在想用怎样的方式走近你,用怎样的乡音土语和你作第一声问候。忽然间我感到了羞惭,我对你一无所知。
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你告诉我,我想知道你的村庄有多大,有多少院落,有多少人家,那院墙,还是不是梦里见过的土黄色。我想知道村庄里的路有几条,那条通往沟底野枣林的小路还在不在,那条路有多长。父亲当年走了多久,看到了那片野枣树。
我想知道祖先的牌位立在了哪里,祖辈的坟茔又安放在何处。我想知道父亲的老屋还在不在,他当年背野枣的那个藤筐,是不是还挂在老房那根最粗的梁上。
我想知道村头那棵护村的老树,那棵树冠如华盖如美丽云裳的老树,是古桐还是老槐。当年的父亲,是不是从这棵老树下离开的,我真的想知道,当年他走过这棵老树的时候,有没有一步又一步地回头……
我来到村外,去看那一望无际的庄稼地,我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想知道那分割麦田的陇道有多宽,乡亲挑着一担麦秸,走在上面是不是比较轻快。我想知道麦秆下面的青虫,开心的时候是热烈地蹦跳,还是腼腆的匍匐,麦苗在节节拔高的时候,是不是欢喜地想哼唱出来。
我想知道,那麦穗初熟的时节,拔一绺浅黄又泛着青绿的麦穗,搓揉掉嫩薄的麦皮,放进嘴里细细咀嚼,那浓稠的麦汁在四溢,那满口的爆浆,滋味几何?
我想知道,五黄六月的开镰,乡亲是不是朝圣般凝神专注,又隐隐地欣喜,清晨麦秆上的露珠,折射出晨阳的浅红和麦穗的金黄,还有田埂边丛丛青草的嫩绿,透着晶莹五彩的光,一闪一闪地亮着,这是真正的斑斓!
晨风中飘泛起成熟麦子的清香,壮实的麦秆上结满了圆圆鼓鼓的穗头,煞是饱满的穗头,像串串金色的汗珠,一穗穗、一行行、一垄垄、一片片,摇曳着,仿佛是在织就一幅金灿灿的云锦。初夏的风一阵阵拂过,麦浪来了!
我看到了麦浪,一层又一层的麦浪,一波又一波的麦浪,像踩着鼓点,欢快地向我涌来,就像是村庄在向我呼唤。麦浪起伏着,一波连着一波,向麦田的四周涌动着,向前方的山峦涌动着,那边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麦浪在高原之间,在一道道沟壑之间起伏着,滚滚地向前方涌动着,像从上游奔涌而来的黄河,继续向前,向更远的天际奔流着。
高原的天空弥漫着成熟的麦子那醇厚的浓香气息,乡亲挥舞着镰,像水手一般在麦浪间穿行着,有一群群鸟儿在啄食着撒落的麦穗,不忘欢快地鸣叫着……这就是我的村庄,这就是我亲爱的村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