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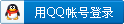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儿时的年味
李新潮
又要过年了,刚上二年级的小外孙放了寒假。一天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爷爷,你们小时候的年是怎么过的?”
孩子的一句话,把我的思绪拉回从前。我属于“50后”,是在农村长大的,儿时的经历正是20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物质虽然不是很丰富,但年味还是很浓的。人们辛苦劳作一年,终于等到过年可以歇一歇。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放寒假了,没有作业的压力,也没有什么网课、辅导班,除了帮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就是尽情地玩,疯一样地“闹”。
在我们晋南农村,冬季农闲,一进入腊月天,人们就开始筹备过年了。那时候,每到年跟前儿,父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养了一年的猪拉到食品公司卖掉,卖的钱除去还掉当年的外债,还得预留一部分作为来年的开销储备,剩下的就用来置办年货。母亲和我的任务则是“淘麦”、磨面(那时磨面用的是石磨子,小麦要用水淘洗干净再晒干才能磨)。小时候虽然年年家里都养猪,但平时很少吃到肉,只有过年时,父亲才会从集上买回几斤肉,用来待客。白面馍平时也很难吃到,常年吃的都是二面馍(白面加玉米面、白面加高粱面)或“黑馍”(和现在人们追求的“全麦面馍”差不多)。
过了腊月二十三,我就开始帮助母亲给家里来一场大扫除。屋里屋外、角角落落都要打扫干净,把上一年贴的旧年画揭下来,换上父亲赶集买回来的新年画。糊窗户纸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家里都是老式的格子窗和格子风门,数量又很多,每次都累得我腰酸背疼,有时天气太冷,抹糨糊时手指头都会冻僵。
过年蒸馍、炸油饼是一件很隆重的事,都要在年前几天做好。老家传下来的风俗是过年走亲戚要“提馍”,这种馍不同于平时家里吃的馍,叫“大馍(土话叫tuo馍,个头比平时吃的馍要大几倍)”,是用母亲磨面时收的头茬白面蒸的。我家亲戚多,每年都要蒸上好几锅。蒸馍技术含量很高,掌握不好会开花裂口。母亲在这方面是个高手,每年蒸出的大馍又白又大,馍面光滑细腻,像绸子一样,常常受到亲戚们的夸赞。
炸油饼我们土话叫“煮pia tuo”,简称“煮油”。油饼主要是留下来过年待客和自己吃的。除了油饼之外,每年母亲还会炸一些小麻花、麻叶和“煮角子”。老家的小麻花与现在街上卖的不同,是用擀好的面片,切成一种形状,然后再把两小片翻成花状黏在一起,下锅炸,炸出来的麻花又香又酥,是那时家家户户过年待客必备的一道美食。
小时候“煮油”时感觉很隆重,大人不让小孩乱跑、乱说话,还要关住院门,防止外人闯进来,说那样的话就会费油。因为那些年油很少,每人每年才能从生产队里分到一斤多油,大多数家庭都是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点油,为的是过年能煮上一次油馍。老家有一个风俗,如果谁家里当年有了“白事”,过年是不能“煮油”的。我想一方面是表达对故去亲人的尊重,另一个主要原因还是缺粮少油的缘故。
老家的风俗每年除夕早上,要先给祖先上坟。过年了,得给死去的亲人们烧点纸钱,也让他们过个好年。小时候都是父亲带着我去上坟,大一点了,每年就由我和堂弟去。除夕中午照例是要吃馄饨的,做饭是母亲的事。午饭前一定要先把对联贴上,这件事从小到大一直是我来干。早期伯父在世时,每年的对联都是他写的。老家是旧四合院,房门多,每年都要写很多对联,大门、院门(二门)及上房、东西厢房、南厦,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要贴上对联。院门上还要贴门神,屋门上还要贴斗方。另外还要写很多小条子:炕墙上是“身卧福地”、风箱上是“风如雷吼”、箱子是“新衣满箱”、面瓮上是“细水长流”、院内是“满院春光”、院外是“出门见喜”、就连门口的大树上也要贴上“根深叶茂”......
小时候,老家在除夕晚上没有吃年夜饭的习惯,注重的是初一早上的年饭。
除夕晚上,父亲一般都在忙着煮肉,肉煮熟后还要给肉皮用熬好的红糖上色。母亲则是和面捏馄饨,为初一早饭做准备。过年的馄饨和平时吃的不一样,叫“花馄饨”,母亲捏出的花馄饨小巧玲珑,好看又好吃,我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因为母亲不吃肉,故而我家的馄饨都是素馅的。与别人家不同的是,吃馄饨要浇“臊子”,“臊子”内容很丰富,除了蔬菜、豆腐丁等以外,荷包蛋必不可少,每人还要外加一个煮鸡蛋。
那时候没有电视,累了一天的我早早就钻进了被窝。父亲在大家都睡下后,还要在门框上插上柏树枝,并在门口、窗台撒上白石灰(或者草木灰),把门、窗围起来,说是这样能防“年”进到家里。同时在院中间用灰撒成一个粮囤的形状,里面画上麦子等,再画一个朝里搂的耙子,寓意来年五谷丰登、财进家门。
初一凌晨,天还没亮,我就被炮声叫醒了。老家过年讲究看谁家年饭吃得早。因此,父亲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先在院子里放一个炮,还要用柏树枝和干草点上一堆火,母亲就开始做早饭。当我起来穿上放在枕头边的新衣服时,母亲已煮好了馄饨。给祖先、灶王爷献完馄饨后,就由我来点鞭放炮,这时候周围的鞭炮声陆陆续续都响起来了。那时候的鞭炮都是黑色火药做的,鞭也只有几百响,小炮有单响和双响的,双响炮也叫“二踢脚”。小时候点鞭炮时,我总要偷偷摘下几个来,然后把鞭挂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点响后还要在院子里转一转。
天亮后,我们几个玩伴先忙着到各家院里去找没有炸响的小鞭炮。那时鞭炮质量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捡到许多没有了炮捻子的小鞭,然后把它折断,用香火点燃,喷出火焰,我们称它为“放花子”。还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如把它摆成一圈,点燃一个,就能引燃一圈。如果有带捻子的,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圈里,花子燃完还带一声响。有时候还会把两个带捻子的小鞭接到一起,自制一个小“二踢脚”。
初一早上,照例晚辈们是先要到长辈家里去拜年的,不等仪式结束,我们这些孩子就自己跑去“疯”了。村里有打麦场,女孩子玩“踢瓦”,男孩子玩“打拐”,后来也有打扑克的。还有的在麦场里学骑自行车,一个村里没几辆自行车,在打麦场里学骑车子,是最令大家羡慕的。那时没有小车子,都是大人骑的车,我们小孩子个小够不着,学骑车时,先是“靠”,然后才敢“拐”(因为个低,上不去,就把一只脚从车梁下面的孔里塞过去,蹬住另一个脚踏子)。有些大人学车子,急于求成,先骑上去,让一个人在后面扶着,骑上几圈后,后面人一撒手,他害怕了,不会捏闸,停不住,下不来,一头冲到麦秸垛上。
村里有个锣鼓队,还有耍狮子的,初一这天,他们会到一些新盖院子的人家里敲打“热闹”一番,俗称“踩院子”。能到谁家,这是很荣幸的,也是讨个吉利,主人会高兴地给他们发一些花生、糖果、香烟,再给一个“红包”。
过了初一,就开始“走亲戚”了。那时交通、信息都不是很方便,亲戚们平素很难见面,过年走亲戚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和机会了。每年都是父亲带上我出去,而母亲则留在家里待客做饭。我家亲戚多,有些家族大、户数多,出门要拿很多馍。家里没有交通工具,出门全靠两条腿,有的亲戚家离我们家十多里路,有的还要翻沟过涧,跑一趟实在是累得够呛,唯一能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去亲戚家能收到一些压岁钱,虽然每人只有一、两毛钱,走完亲戚,每年我都可以攒好几块钱。
老家的风俗和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初二是先走舅家(结婚后即先走岳父家),然后是姑家、姨家、老舅家、老姑家……过了初五,还走不完。人们“走亲戚”都是走路,背着包馍的红包袱,南来的、北往的、东走的、西行的,大道小路,一行行、一群群,很是热闹,自成一种风景。
过了十五元宵节,这年才算过完。
记得有两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提出口号“腊月三十不停工,正月初一开门红”,大人们要忙着劳动,但对我们小孩来说,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闹闹,年味仍在。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序的变化,物质越来越丰富了,交通越来越方便了,尤其是有了网络、快递、“春晚”……和过去比,好日子天天都跟过年似的,然儿时的快乐不再,年味也越来越淡了。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了,乡愁依旧留在记忆里。我们这代人依然执着地想把“过年”这一传统文化坚持下来,一代代传承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