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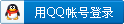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我的大山,我的牛
胡春良
五月的柴家沟,小河在青草芽间穿行,荒地上长满蒲公英。我就躺在老田门口的大石头上,望着山头的白云出神,鸟儿在老柳树枝丫间叽叽喳喳说着知心话。这太阳也真是的,要回家了也不打声招呼。猛然坐起,环顾四周山林草地,五头牛一头也不见了。一跃而起,大声呼叫我的牛。除了山野空谷的嘲笑一般的回声,什么也没有。这一急非同小可,我惊醒了,原来是个梦。遥想中条山,思念故园,不禁怅怅然。
我的家乡在中条山深处的太宽河边,小村只有十五六户人家,七十余口人。小村的牛呢比人还多。童年时,除了帮家人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外,我主要是放牛。一般是三两个成群结伴放牛,有时是多半个村的牛都集中在一起,牛叫人欢好不热闹。牧歌童年,别有一番欢乐!
说起放牛,我们村有两个放牛老把式。一个是我爷爷,他脾气暴躁,又不多说话,他放的牛都非常听他的话,但小孩子一般不喜欢和他一起放牛。另一个就是我外祖父,他经历磨难多,见多识广,而且热络,小孩子放牛都喜欢和他一起。外祖父不仅对家乡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都熟悉,还会根据牛蹄判断是哪一头牛。同时,他也是拾柴的高手,总会帮我们把柴捆得紧紧的,而且会把挨肩的部位处理得非常到位,背在肩上十分舒服。往往是外祖父带着我们三四个小鬼在山间放牛。只要有外祖父在,我们大可放心。
那时,每家都有五头左右的牛,多的有七八头。由于山林茂密,特别是夏天,一旦牛钻进树丛中,看不见,也不好找,所以基本上每头牛的脖子上都挂个铁的或铜的铃,我们习惯称之为牛铃。牛吃草或行走时,铃就会响个不停,即便看不见牛,我们也能知道牛所在的方位。放牛时,群牛铃铛响个不停,像是朴拙原始的交响曲,很是热闹。春夏秋三季放牛,早上放一次,午饭时赶回家,下午再赶到山上,傍晚再赶回来。如果是农忙时节,一般早上把牛赶到山上,就回家了,任牛自由活动,下午再去把牛找到赶回来。有时十天半月就散放在山上。基本上每家牛都有头牛,其他牛会紧跟它。经常在一起放的牛,基本上也会一起活动,当然,其中必有一头公认的头牛。冬天放牛简单些,早上太阳出来后,把牛赶上山,然后回家,一般天黑时,牛就会成群自动从山上回来,我们一般只在村口等就行,它们会自觉回到各自圈中。
放牛无小事,牛是全村的大事。一旦牛在山林中找不见,特别是两三天不见踪影,全村人都会自觉去找。如果是晚上,每个人或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腰上别把斧头,再带上自家的狗,在山间小路、山林深处寻找,直到找到为止。这份温暖的情义是小村的良知,是小村的热诚,是小村大家庭的爱。其朴素、其自觉,令人久久怀念。
放牛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拾柴禾,我们土话叫背柴。柴是各家生火做饭、冬天取暖烧炕的必备之物。我们只拾干柴,山林中枯死的树枝、树干是首要选的。我们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拾取干透了的、光杆的、易燃耐烧的。干透的杜梨木、青冈木、橡木、豹榆木,还有杨木都非常受欢迎。有时也专门找黄栌木,因为它生火容易。把柴禾用斧头砍削整理好,用自带的绳,或者就地取材用葛条、羊角蔓、山葡萄藤等捆紧,赶牛回家时背回去。背一捆柴,往往要走上好几里路,如果牛跑远了,十里八里也背。柴家沟、李家沟、韩家洼、上岭、韩家洼后沟、王家坡岭等地,都炸响过我们放牛的鞭鞘声,也留下了背柴的身影,那时也不觉得累。一般一个寒假背的柴够家里烧半年。谁家的孩子背的柴多、柴好,似乎成了家里的脸面。我背柴是比较拼命的。妈妈身体不好,还要忙庄稼活,我就为妈妈背最多最好的柴。别人一般一天背两捆柴,我平均每天背六捆,肩膀红肿,腿上也满是划痕,也不觉得苦累。
耕牛刚由生产队分放到各家各户的那个暑假,我和保平、香会、军国等几个经常把牛赶到李家沟放,每天早上赶到那儿,晚上赶回来。有时傍晚把牛集中在一起,不往回赶,我们也就回家了,牛就在大树下过夜。说起那个暑假,我们还挺“糟蹋”人。正值核桃有嫩仁时,我们或爬上振学家,或香会家,或我家地头的大核桃树上,采摘最好的核桃,用八号铁丝自制的小刀剜核桃吃。先把核桃弄成两半,然后旋出核桃仁,大饱口福。几乎李家沟每棵核桃树下都留下我们的杰作——核桃瓢。当然,这事被大人们知道了,我们免不了会挨打受罚的。
说起放牛,我们还遇见过极其悲壮震撼的牛集体悼念仪式呢。开军家有一头黑狸毛大公牛,极其彪悍,生性好斗,而且十分活跃。若到发情期,它更是近乎疯狂。那天,我们从韩家洼放牛归来,三四家的牛共二十多头,那黑狸毛大公牛不是爬跨到这头牛背上,就是爬跨到那头牛身上。正当从阳坡顶崖跟狭窄小路上经过时,那公牛一爬跨,那母牛闪了一下。在我们的惊叫声中,那公牛滚坡了,跌落到三四十米的深沟里。沟里是条小河,大杨树下有个深潭,牛正好掉进潭里。那牛挣扎着起身,口吐鲜血,但仍然向前奔跑,又跑出约五百米时,竟然在太宽河水磨潭边的开阔草地上气绝身亡。群牛疯狂地围上来,仰天嚎叫,前蹄刨地,草叶草根、沙土沙石乱飞。尔后,有的牛前腿跪地,凄厉嚎叫,有的牛就在草上打滚,任凭我们用木棍赶也赶不开,就连我那放牛经验丰富的外祖父也束手无策。嚎叫声引得全村其他牛一起呼应。之后,人们把那头死牛抬走了,群牛仍久久不愿离去。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每每经过那里,群牛都要举行特殊的悼念仪式。牛之间的真情和悲痛真切得让人震撼,那是生命的原始抒发。
放牛呢,还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牛糟蹋庄稼。那些牛都精得很,哪里有庄稼,哪里能进到庄稼地,哪里能偷吃上,那些头牛、那些老牛是非常清楚的。有一年冬天,我和外祖父早上把牛赶到十亩地岭,背捆柴就回家了。下午晚去了会,二十几头牛全部跑到庙前村一户人家的麦地里啃麦苗。那位老人气急了,把牛全部赶到他们村,圈到一块空地里还不解恨,又拿着根木棍追着打。照例是外祖父出面协调,赔情说好话,我们才把牛赶回村。少不更事的我们嘲笑了那位老人好长时间。
放牛之乐,还有打猎之趣。当时家家都养狗。放牛时,狗也跟着上山,几家牛一起放,几家的狗也一起上山。经常遇到几条狗向野猪发起进攻,大多数情况下,狗是奈何不了野猪的,我们喜欢的是那份热闹。这些狗中,有许多是出色的猎狗,我家的小黄狗、雪旺家的大黄狗就猎获很多,猎物主要是獾,偶尔有野兔和野鸡。獾一般下午都出洞活动饮水,特别是秋天,往往放牛归来,我们肩上扛的不是柴禾而是獾。有一次在韩家洼后沟,天黑了,我家还有一头牛没找见,正在急头上,小黄狗却和獾干上了。为了找牛,我也没顾上帮忙,小黄狗居然猎获了两只獾。这条狗的名头还是很响的。雪旺家的狗也经常在柴家沟、春沟一带猎获獾。我们往往希望多带几条狗,放牛时捎带打猎,就为好玩。打猎也是不那么容易的,这些猎狗经常是满身伤痕,但充满着狂野的力量!当然那时还没有动物保护意识。狗还有其他作用呢,它会顺着牛留下的气味帮人在山林中找到牛,遇到蛇什么的,也会勇敢地冲上去。冬天下雪路滑,如果摔倒了,我家的小黄狗还会咬住衣服拉人起来呢,通人性啊!
放牛还有采摘之乐。一是采挖药材,有连翘、丹参、黄芩、桔梗、苍术、柴胡、五味子等中药材;下雨天可以采木耳;春夏之交可以采食大琏(一种野生果);夏天可以采食菠盘(一种野生草莓);秋天呢最美,许瓜瓜、山葡萄、野李子、毛栗子等等都是美味。我们也经常采挖野菜,比如小蒜、山葱、山韭菜、香椿芽、羊肚菌等等。反正放牛时是不会闲着的。
人有英雄,牛也一样。在这里,我就说说几位牛英雄吧。第一个当属“白点点”。那是一头雄壮健美的大公牛,堪称牛群的“著名演员”,荣幸的是分给了我家。它因黑红毛色,夹杂白斑点而得名。它长着一副美丽的大犄角,勇武异常,鲜有对手,每每在山林中穿行,虎虎生风。它也是犁地耕田的好手,深得人们喜爱。我家人把它照顾得特好。可惜的是,第二次分牛时,它被分给振学家,一年后被卖给杀牛的了。这让我痛惜了好长时间,我真不敢想象屠刀怎么忍心刺进它那俊伟的身躯。
第二个是“老黄键牛”。它身材粗壮低矮、四肢健壮,上坡爬山健步如飞,人称“爬山虎”。它生性更好斗,白点点犍牛有大侠风范,而它呢,堪称绿林草莽,曾经和王家坡的大犍牛恶斗,甚至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折断了双角。自此和王家坡的犍牛不能再见面。“老黄犍牛”和“白点点”合伙耕田乃绝配,其最后也难免年老遭卖,死于屠夫刀下。
第三呢,该说一说“米轱辘”了。它得名于环形的双角和金黄色的毛色。它身材高大,力大无比,加上不好斗,少缺一股狂野霸气,但耕田也是绝好把式,人们也颇为喜欢。
第四呢,当属“白涅(音)”,这是土叫法,“涅”指额头,因额头上有一撮圆形白毛而得名。这牛最大的特点是腰特别粗,人们都称其油桶腰,颇有蛮力。其两角水平生长,却少点雄风。这牛耕地很好,偶有打斗,打斗中失去一角。一般牛不敢惹它,但它天生就怕“白点点”,一见面就躲开,往往会被追着跑。它们耕地根本驾不到一块。
熟悉的中条山,熟悉的大黄牛,童年牧歌,是生活的原生态,是行云流水的记忆。也许我们每个生命都渴望一种与自然相谐相融的自在境界吧,所以放牧的童年,也被童年所放牧。这是一份道法自然的真纯,也是心灵本源的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