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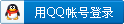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清明泪
王西兰
又是一年清明节。
头一天我就准备好祭品:纸钱、香火、供献。看一眼母亲的遗像,母亲神情依旧,一双细眼里流露出要与我诉说什么的神情。我就和母亲开始心灵对话:
“妈,我明天回村去为你上坟。”
“不,不要。”
不,我要。别说几十里乡间土路,就是翻山越岭、跨江过水,我也要去为母亲上坟。既然母亲栖身在那一片偏僻的墓地里,我就注定这辈子得经常走过这几十里土路,到那片坟场里探望母亲。
母亲得的是脑血管病,说话口齿已经不清,思维也常常糊涂。可有时说起身后事来,却十分明晰:
“我死了,你把我火化了,装一个盒儿。今后你走到哪,就把骨灰盒带到哪。”
我笑着顶她——母亲语言能力下降后反而愿意与我多说话,而且不爱听我用那种给病人的慢声细语或敷衍应付的语气,仍要我用过去母子间毫无障碍的口气说话——
“火化?你不是说新社会啥都好,就是火化人不好,怎么要火化?”
母亲被顶得没了话,仿佛输了理似的笑笑。一般情况下母亲被我问住了反而显得很愉快。她喃喃一会,才又说:
“可你回村里一趟太难。”
母亲是说我的晕车。
我从小就晕车,据说小时候坐马车也吐得昏天黑地。这是母亲说的,我自己已记不得,但直到如今坐一趟汽车仍然就像害一场大病。说是怕颠吧,在溜平的柏油大路上也晕。说是怕汽油味,坐电车倒没汽油,照样晕。那年第一次去北京,听人说四路环行车可以一览北京市容,于是试着去游览一下,谁想不到终点就连爬带滚地下了车,顺势躺在那车水马龙的长安大街上,引得路人围了里外三层,惊动了警察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件。
在卿头下乡,回县城等车就在卿头镇村南大路口。那里公路往东几里外是个大大的深坡儿。东边来了车,村路口远远只见尘土扬起老高,半晌还不见车来。可我只要看到远处尘土飞起——车还早着呢——就晕了起来。有一段时间给一位领导当秘书,常要随领导跑乡下,一见通讯员来说“八点钟去某某公社”,我就开始晕了。其实我住东院,领导住西院,车库还在西院的西边,这当儿车库的门还没开呢。所以到县城工作后,回一趟家,几十里路就视为畏途,摇摇晃晃走进家门,往炕上一躺,翻肠搅肚,疲脸慌汗。母亲就急着开罐头,说那东西能治恶心。我倒是常给母亲买罐头,可多数还是我吃了。
原来母亲说要火化,是怕以后我回家晕车:“活着的时候那是没法了,你得回村来。可我死了咋还叫你受那罪?你把我火化了。”
我说不行。尽管如今提倡火葬,可农村里还没有实行。当真把她火化了,村里人议论我就受不了。她知道我就不是个敢作敢为的人。
母亲当然了解我,而且她本来就害怕火化。于是沉默半晌,才又说:“那么,我死了,你就别再回村里来了。”
——怎么能不回来?逢年过节,我得给母亲烧纸。母亲爱花钱,没有钱怎么得了?
“钱要烧。你就在县城里烧。”
“县城里怎么烧?”
“你到城外找个十字路口,划个圈儿,在咱村方向留个口,把纸就放在那圈儿里烧,我就收到了。”
“要收不到呢?”
“心到神知,收得到。再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你要烧纸,就格外留心着,怎么会收不到?”
“只要能收到,我就多烧些。”
“只是你不要用那铁凿儿打纸钱印,把白纸裁裁割割就行了。”
“不打钱印,一张白纸哪能花?”
“能花,说不定那白纸倒是个存折,十万、八万的呢——在机关里打纸钱,人家会说你迷信。你心思小,受不了一点意见。”
虽然是说着笑话,我已经听得潸然泪下。一见我流了泪,母亲还要责备两句:“男娃,没一点刚强。”我就尽量忍住,尽量别在母亲面前流泪。
半年后,母亲去世。我当然没有勇气把她火化,只能随乡就俗地把她安葬在村里那片公共坟场里。我也没有照着与母亲的约定去十字路口烧纸,不管她生前说得如何肯定,我都觉得她收不到。十字路口,八面来客,怎么就能收到?
母亲是城市贫民出身,知道街市上没钱的难为,回到农村几十年也改不了小市民的老习惯。村里人没钱照样过日子,两把柴火几苗青菜,田间地头转一趟就拿了回来。可母亲一旦手里没了钱就惶惶不可终日。每次我回去她不明说要钱,只是唱戏:
“儿做了官了,娘要了饭了!”
这是《放饭》里的戏词。母亲年轻时爱看戏,三折五本可以倒背如流,要表达什么意思,随意就可在哪本戏里找出对路的词儿来。我就赶紧给她留钱。她也不多要,三块五块就行,小富即安,典型的农民或小市民意识。也许大雅似俗,要的只是一种儿子留钱的感觉吧。
母亲花钱的出路很多,多数是花在孙子身上,“孙子给我要钱,我说没有?这奶奶以后咋当?”她经常坐在巷口打听谁去县城:“你替我去一趟学校,看看我孙子好着么。见一眼回来报个信就行。这是车费,这是一顿饭钱。你别去家里找,机关事多,顾不上给你做饭。”再就是赞助别人。偶尔来一两个讨饭的,除了给人家吃饭,走时还要给带上两毛钱:“你如要赶路,两头赶不上顿咋​办?”
实际上讨饭的哪还能按顿吃呢?
那年我领她去西安看病,下了火车只见许多残疾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伸着手向旅客要钱。别的旅客匆匆出站,眼前推不过去的才给。母亲倒像是机关事务长发福利,人人有份,跑东跑西地奔到那些残疾人跟前,每人两毛。有的离得很远,也要赶过去不让把谁空下。说,近处都有了,远处那一个没有,心里不难受?还说,一毛钱拿不出手,再多了我也没有,两毛就合适。你想她兜里怎能没有钱?如今母亲死了,我更不能让她手里缺钱花。村里的家上了锁,我在县城住,逢到节气,我就回村给她烧纸去,也顾不得晕车了。何况每年就春节清明那么两趟,再晕车我也得回去。
清明这天一早,我就收拾停当,乘车上路。一路上阳光和煦,东风送暖,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桃花红,杏花白,桐树花儿淡紫淡紫;麦苗儿青,菜花儿黄,刚绽开的杨树叶儿翠绿。
空气湿漉漉的,润人肺腑。我无心欣赏这些,只想着母亲坟头的迎春花儿可曾开了?去年上坟,见人家坟头迎春花开得正闹,母亲坟头却光秃一片,心中不安,后悔自己没有及早栽些这种丛生植物。趁着没人注意,偷偷从别人坟上挖了几枝移植在母亲坟头,又不能浇水,也不知活了没有?还有坟场里最讨厌禾鼠打洞,那片坟地里禾鼠却又极多。去年县上曾布置全民灭鼠,田间的禾鼠不知道可曾根绝?
胡思乱想,没头没绪,不觉到了村口。我顾不得去谁家小坐,也顾不上与村人在路边寒暄,从近处人家要一把铁锨急忙就上坟地去。已是春耕大忙,路上行人三三两两,都是急急忙忙地上地赶活,一路也就没啥耽搁。不多一会儿,就赶到母亲居住的坟地。
母亲的坟头显得朴素而荒漠,不似周围许多老坟那样破败,也不似几捧新土那般鲜丽。比起那些老坟的萋萋青草,它显得单薄,只有稀疏的几枝迎春花点缀着零星的黄骨朵儿;比起几堆新坟上那尚未败落的花圈和纸幡,它又显得贫瘠,只有坟前一株小松树在春风中摇摇曵曳。这就有些像是母亲生前的做派,不着意收拾又绝不邋遢,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样子。坟头一圈麦苗长得茁壮,像一个巨大的绿色花环。坟头和边上也没有鼠洞,只有雨水冲刷的道道痕迹。我用锨在周围铲了土,仔仔细细地把坟头培好,母亲的坟茔就又显得整洁如新,我想她看了一定会十分满意。母亲爱洁净,常常对我说:“笑脏不笑破。”也不知这是哪出戏里的词儿。
忽然,我发现母亲的坟头缺少一样东西:一张压坟的纸条儿。我们这地方的风俗,扫墓上坟烧完纸钱以后,都要在坟头上压一张纸条儿,仿佛是这坟里的逝者后世有人继续香火的标志。农忙时节,上坟赶早,这时候已近中午,村里人全都已经上过坟了,坟场上每一个坟头上都压了纸条儿,飘飘拂拂很自豪的样子,唯有母亲的坟头还是空白。我不禁替母亲感到难堪:母亲一辈子命运多舛却又争强好胜,不论啥事都不甘人后。自己吃苦受穷倒没什么,就怕人前没有面子,把那虚名儿看得要紧。人家坟头上都有纸条儿飘拂,而母亲却没有,怎不叫她心中难受?好在我回来带的祭物非常丰盛:一把线香,几样吃食,一沓各种式样的纸票。这种纸票是我们这地方通用的冥钱,刻版印制,面额多为大额,一张都是一百万元。
我在坟前焚了香,摆好供品,然后慢慢地烧化纸钱。除了那些百万大钞,我还为母亲准备了些小额票子:二十元、十元、五元,免得为那些大票子花起来不好找零而受了作难。我想,这一片坟场虽然只有我因路远扫墓来迟,可我准备的香火供献肯定是最丰富的,这就足使母亲心里得到一些安慰,让她那可以原谅的虚荣心得到平衡和满足。一张张纸钱渐渐被火舌吞没化为灰烬,黑色的纸灰像一只只大蝴蝶似的飘向坟场的上空,越飘越高,越飘越远,一直要飘向母亲灵魂居住的天国。
这时候整个坟场一片凄冷静谧,那么多坟头下的每一个灵魂都善解人意地安息着,不来打扰我们,让我给母亲诉说心中无限的思念。我心说:妈,这些钱你都收下,想花你就花,不要受屈。如今咱有钱,连你百般疼爱千般呵护的孙子孙女都挣了钱。啥时花完了,再来给你烧……
鸟儿不飞了,树儿不摇了,太阳躲进云里,春风绕了道儿。满世界都好像静止了,偌大的坟场,只有我与母亲用心灵对话。
我们谈了很久、很久。
回来的路上,车子开得风驰电掣。我坐在车上,又好像不知身在何处,思绪还留在母亲的坟前,仿佛看见母亲刚刚收到了钱,欣喜地把整票儿放在箱底,零票儿压在枕下……
忽然,车停了。
到了?怎么没觉得,就到了?下了车,头上,有微微细雨。脚下,是湿湿的土地。噢,清明时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咦?我好像、好像——
哦,今天我没晕车!
往常要坐车出门,提前就做好一级战备:吃晕车药,抹风油精,肚脐上贴橡皮膏,嘴里含茶叶,手心里抓把盐,可晕车还是不能完全止住。今天去给母亲上坟,只顾张罗祭品,早忘了那些战备物资。来回百余里乡间土路,却竟然没有晕车!
两行清泪泫然流下。噢,我知道:
母亲,是你在护佑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