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开启数字生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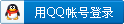 
×
历尽坎坷 不改初心
——记我的母亲樊桂英
罗力立
20年前,重度中风、在病床上不会翻身、不能说话、和死神抗争了近十年的85岁的母亲,终于撇下了我,永远地走了。
出殡那天,她身上覆盖着印有镰刀锤头的党旗。我注意到,她的遗容非同一般:非常洁白,耄耋之年竟没有一点老年斑,就像她生前的心境一样冰清玉洁,就像她的人生一样纯正无邪。
她已经去世20年了,可她在病中一次次呼唤我,我坐在她身旁,一口口给她喂饭的情景,还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一
母亲樊桂英,1916年出生在安邑县一个普通农家。兄弟姊妹8人,她最小,总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小学毕业后,她到运城上了女师。她爱读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思想活跃。因反对会考,闹学潮,她被父亲幽禁在家,不许继续升学。可是母亲渴望求知,我善良的外婆便偷偷卖掉自己唯一的私产——一个三钱重的金指环,让她当路费跑到西安考取陕西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半工半读。
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洪流的影响,她于1936年12月初参加了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请愿大示威,还和6位同学一起参加了绥远抗战慰劳团,路上被“中央军”四十军扣留,后乘机逃脱。双十二事变后,她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她从助产学校毕业后,留在学校附属产院服务。1938年,住院产妇刘群先(博古的爱人)介绍她到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中共中央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是胡乔木。在这座革命青年的熔炉中,她学习马列主义、抗战理论,思想产生飞跃,确立了信仰,后由吴仲廉、张杰二位同志介绍,于1938年2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党派她到甘肃兰州参加地下党甘肃省工委工作,担任工委妇女委员。为了工作方便,党决定让她和工委副书记罗云鹏假扮夫妻组成家庭,以做生意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经过5个月“假夫妻”生活,他们相知相爱了,并由谢觉哉介绍,结为真夫妻。当时的罗云鹏刚届而立之年,却已是资深的地下工作者了。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便入党,并被捕入狱一年多,出狱后调上海、青岛、大连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结合很简单,没有华丽的爱巢,从未拍过合影,但共同的理想志趣,为他们缔造了坚如磐石的爱情。他们在各方面取长补短,生活虽然艰苦,感情却十分美满。1939年9月,母亲生下了一个8斤重的胖胖的女婴,就是我,取名罗俐丽。
然而,不幸的事突然发生了,1940年6月6日凌晨2时,父亲和在我家开会留宿的工委书记李铁轮、工委青年委员林亦青3人一起被捕。本来母亲有充裕的时间抱着我跑到八路军办事处,那就安全了。可她放不下丈夫和同志,到看守所送饭,又抽空烧毁藏在家里的党的文件、资料,直到两天后才欲抱着我离开,也不幸被敌人抓走。
我们被捕后,共转移了4次,最后被关在偏僻的兰州沙沟秘密监狱,一关就是6年。父母亲多次被酷刑折磨,父亲在狱中曾患伤寒病,两度失明。但他们始终坚强不屈,在狱中成立党小组,鼓动难友越狱。母亲还常给难友缝补衣服。
有一次,敌人提审母亲,要她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她和已暴露身份的罗云鹏脱离夫妻关系,并给她十指钉竹签,加以威逼。母亲几次昏厥过去,醒来后不断呼喊:“他是共产党,我不怕,我不会离开他……”当她回到号子里时,我从土炕上掉下来,哭哑了嗓子。母亲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抱起我,母女的泪水融汇在一起。
1946年2月27日,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活埋,时年37岁。临刑前,敌人还在劝降,父亲慷慨陈词:“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他对党的忠诚动天地、泣鬼神。从此,7岁的我失去了父亲,30岁的母亲失去了丈夫。父亲牺牲前嘱咐母亲将我的名字“罗俐丽”改为“罗力立”,这个名字赋予我们面对厄运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引领我们在任何逆境中都要有力量站起来。
同年8月,敌人在清理积案时,由于缺乏母亲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便让她填了一张开释表,将我们释放。
1947年4月,母亲带着我到西安投奔我姨妈。姨妈年轻守寡,有4个孩子,经济困难。为了生存,母亲得想法赚钱。得知当时陕西省立医院需要助产士,但条件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能入职,她只好托老同学弄了一张假国民党员证,才得以入院工作。
在这期间,她到陕西耀县四哥、四嫂家去过。耀县是紧靠解放区的拉锯地带。她四嫂加入一贯道。母亲听她说,该道中有人常到延安、洛川、宜川等地去传道,母亲便混入一贯道,目的是乘机去延安,找党组织。后来她发现一贯道里面有国民党特务组织,人员很复杂,想通过它去延安很困难,便打消了原来的设想。
为了找党,母亲1948年8月带着9岁的我和住在姨妈家的60多岁的外婆,冒着生命危险,一路上受尽兵匪盘剥,渡过黄河,从蒋管区西安回到解放区山西安邑——她的娘家。她找组织心切,回来后很快到县政府找王菁华县长说明情况。王县长热情接待并介绍她到运城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
接着,母亲的狱中难友、共产党员赵子明、王芳、纪宇等人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母亲在狱中6年,虽经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于是,1950年7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决定“恢复樊桂英同志党籍”。
二
回到了解放区,再也没有特务跟踪,又恢复了组织关系,母亲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甩开膀子为党工作了。在担任运城人民医院产科医生期间,她昼夜忘我工作,经常把我一个人反锁在屋子里。
1951年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又派她到运城专署保育院任副院长,后又担任了院长。她熬夜钻研幼教理论,把心思全放在孩子们身上,领导和家长都很满意。
1952年,在审干整党运动中,她本着对党忠诚的态度交代了出狱时填过开释表,没有承认自己是党员,但也未出卖同志和党组织;还交代了在西安为了糊口冒充国民党员的事;还讲了她在陕西耀县参加过一贯道,目的是想借传道之机,到延安去找党。本来这些事都可以理解,但当时组织上给她下的结论是:自首,叛党。
1954年7月31日,中共运城地委组织部作出决定:“为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决定开除党籍。”我当时上初中,不懂个中事由,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很伤心地哭泣。我不敢多问,只能给她递去湿毛巾。这时,她突然仰起挂满泪水的脸,失声地问:“你想不想爸爸?”我说:“想啊!想啊!”我们只能抱头大哭。那时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出现在我们面前,抚慰一下万分痛苦的母亲。母亲是如何努力地克制着内心的创伤埋头工作,十多岁的我还不大懂,我所看到的是,保育院的孩子们个个干净、健康、漂亮、活蹦乱跳;我还看到,络绎不绝的带孩子入住的家长们和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粉碎了,随着我党平反冤假错案的英明举措,年过花甲的母亲的命运才开始有了转机。1979年1月,运城地委将她的右派改正;1981年,母亲离休;1983年1月,她恢复党籍;1989年5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准,母亲参加工作时间由1938年更改到1936年12月,并享受副厅级待遇,成为老红军干部。
她离休后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多么希望她老人家能健康长寿,永远快乐。谁料想在1992年,她突然中风失语,卧床不起,饱受折磨,疼痛发作时,要靠打杜冷丁才能止痛。母亲病重期间,当时的运城县委领导曾多次到家里探望,领导还责成县医院专门成立了樊桂英治疗小组,精心予以治疗。
1994年3月10日,西部歌王、我们的难友王洛宾,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赶来运城看她。她已不会说话,见到王洛宾便失声大哭,让在场的家人痛彻肺腑。
母亲患病后期,我和老伴儿都已进入花甲之年。我身体不好,老伴每晚都多次给母亲翻身、换尿布,因此,母亲卧床10年,从未长过褥疮。周围的人都夸奖,说这样的女婿少有,胜过亲生儿子。
然而,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她的生命。2001年1月30日,85岁的母亲终于闭上了眼睛,走完了她极为坎坷的一生。
母亲的追悼会十分隆重,相关领导亲临会场,并致悼词说:“樊桂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她和家人鲜红的血迹……”
三
母亲的人生是痛苦的,坐牢6年,孀居50多年,由于极“左”路线,她多次沦为被扩大化的打击对象,这对于她的身心健康无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然而母亲是生活的强者。最近我拜访了一位老同志,他是原运城行署卫生局局长吕谦。他说:上世纪50年代,我曾和你母亲一起在运城人民医院工作过,她个头不高,人很精干,穿戴整齐漂亮,工作热情积极,很有朝气,根本看不出来她是个失去丈夫、有“历史问题”的人。
我看过运城人民医院内科原支部宣传委员武香兰在1960年写的一份材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樊桂英在工作中从来都是苦干实干,有多少病人看多少,曾有一段时间,门诊就她一人,每天24小时一人顶。患者给她送来锦旗。在病房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细心,对病人态度好,曾受到病人十多次张贴表扬……”
我的母亲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寄托和意义,她把个人的不幸深深埋在心底,只要有机会给老百姓看病,她就会焕发出火热的激情,忘我地工作。
就在她被定为“叛徒”、每月只发25元生活费期间,她热心为人民看病的信念依旧坚定。1972年,运城县卫生局成立了科研组,医术高明的母亲和另外两位医生是这个小组的核心。她们三人就妇女外阴白斑(属癌前期病变)这一顽症,搞科研攻关,研制出一种中药膏,对治疗此病卓有显效。经病理切片证实,经治疗能使白斑的色素恢复,角化的外阴恢复正常。当时省内外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医院病房和院外旅店里住着很多病人,母亲非常忙碌,经常顾不上吃饭。我星期天带着孩子去看她,总是在病房里找她。病人见了我常说:你妈妈手高、心好,治好我的病,不知怎么谢她……
由于成绩突出,她们科研组这项成果被评为运城科技成果二等奖、山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后来她们的论文《补骨脂浸膏治疗外阴白斑53例》发表在1977年第7期《新医学》杂志上。
母亲不仅热爱工作,也热爱艺术。她书法不错,钢笔字、毛笔字都很帅气。她还擅长编织,我小时穿的毛衣、毛裤、毛袜,都是她编的。她用棉线钩织的桌布很漂亮,我一直珍藏在衣柜里。
我常常思考:母亲太不容易了,忙碌了一生,委屈了大半生,虽然无论政治生涯、家庭生活、社会待遇,长期得不到起码的安宁、幸福和荣耀,还遭遇了人世间罕有的磨难与不幸,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她对事业、对病人始终怀有炽热的情怀,哪怕默默无闻,哪怕被人曲解。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对党、对国家、对生活有过任何抱怨。她从不消沉,性格乐观,在和别人聊天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对人类美好明天的信仰,是对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信仰,是对真理的信仰。
我读过诗人阿紫写的《生如胡杨》这首诗。我常常把胡杨的形象和坚强的母亲联系在一起。母亲不正像那戈壁荒漠中的胡杨一般吗?在风沙呼啸肆虐中,深扎根系,活得筋骨铮硬,活得凛然豪放!她虽然离开了我,但她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