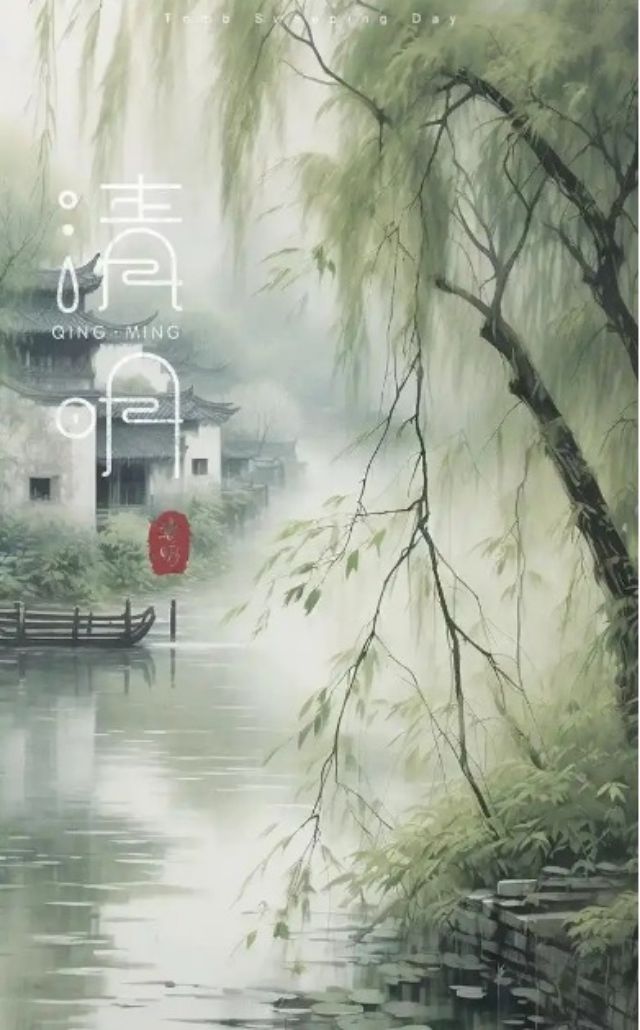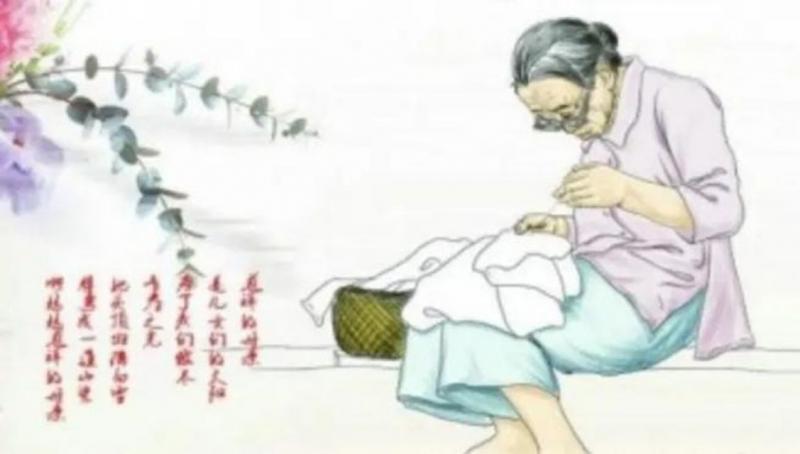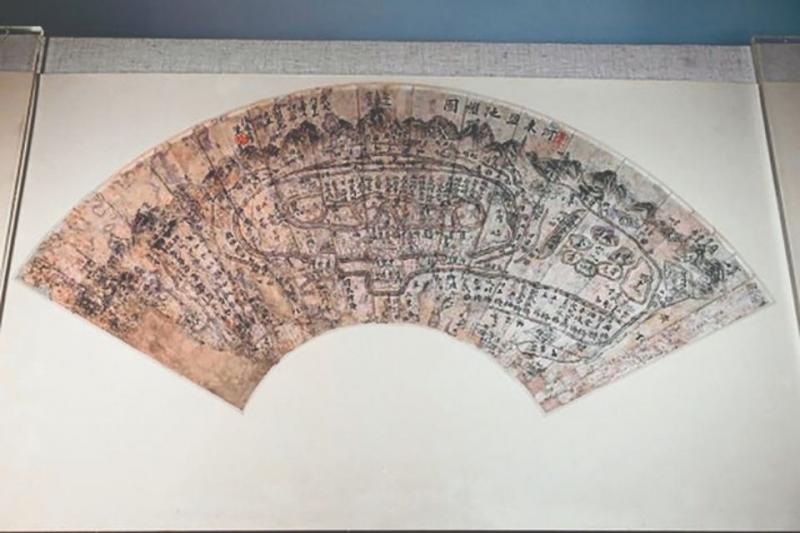河东文学 读韵荷散文《奔跑的村庄》有感_文评_刘锁爱
发布时间 2025-04-02 17:48:18
安全小贴士:以各种理由收取费用(押金、服装费、报名费、充值卡等)均有诈骗嫌疑,请提高警惕。
详细描述
标题: 读韵荷散文《奔跑的村庄》有感_文评_刘锁爱
发布位置:
韵荷的散文集《奔跑的村庄》出版了,这是她继《遇见自己》后的第二本散文集。听说两本书在网上卖得挺好,我着实为她高兴。要知道如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抱着手机刷视频、玩游戏,很少对纸质书感兴趣,而韵荷的散文却很受欢迎,不由让人想走进她的书里探个究竟。
她的书名不虚传,打开就想起“开卷有益”那句话。她的书是引人入胜的、是有趣味的、是富含哲理的、是接地气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的。
她的书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韵荷的散文,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村庄,写的全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是张家大爷、李家奶奶,是你家大哥、邻家大姐,抑或是自家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表哥表姐及远亲近邻的父老乡亲们。
她和她的村庄,是无法割舍的。那是她的根据地,是流淌在她血液里浓浓的因子;是维系她生命里的那根长长的脐带;是她一辈子的灵魂栖息地。她用她的笔触为家乡代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用她的笔写出家乡在发展中的阵痛幽怨和父老乡亲的苦辣酸甜。
她的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一是每一个故事都很生动出彩。她的人物是鲜活的、立体的、独具特色的。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个一个镜头推出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画面感,让读者和人物瞬间融为一体,并带着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其痛痒。
其二是语言具有趣味性和区域代表性。拟人和拟物化的描写,加上典型的地方方言,让语言达到了一种至高至极的纯粹状态,充满了张力,让人物也活了起来,丰富而多彩。她的有些语言和人物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她写爸妈在土地上劳作:“黑褐色的土地被爸妈翻腾得起了‘浪花’,一犁接一犁,牛累得浑身直冒汗,土地乐得直翻滚。路边枝杈上的喜鹊不停地喊:‘歇一歇呗,歇一歇呗!’最懂我的,是那只穿着花衣服的喜鹊。那年,爸妈像是长在了桃园里、长在土地上;忙完了桃树,忙果树;忙完了果树,忙柿子树……”写她在这个桃园看桃时,“像是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哪个桃大摘哪个,哪个桃红吃哪个。吃饱了,躺在树杈间,抱着一怀凉风,闻着桃香,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武侠梦”。她写《菊花嫂子》时这样形容:“她拉着我的手,依然显得敦厚、朴素、实诚。她上嘴唇很厚,向外翻着,熟悉的大龅牙裸露在外,好敬业的哨兵啊!阳光热烈,花草含笑,我们咫尺而立,一股清风在我们之间穿行。”写到菊花嫂子的婆婆肥胖,用了“幅员辽阔”,走起路来“动静格外大”。她的这个语境和独特的比喻,让人物个性顿时活了起来,充分发挥了读者对人物的无限想象,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到菊花嫂子养了一儿一女,女娃长相随了父亲,模样俊俏,温柔娴静,儿子则像她母亲,相貌平平,老实木讷。这时的菊花嫂子眼里噙着泪花说:“让村人见笑了。”而这时的韵荷也笔锋一转,用乡间俚语这样描写:“在村子里,世世代代为邻,谁家锅底没点灰,谁顾得上笑话谁呀!”一句俚语的巧妙运用,让整篇文章有了灵魂,有了生命力。《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里,写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文学女人是她的邻居,“她家居前,我家居后,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土墙很薄、很低、也很脆。冬天,西北风呼啸而来,那墙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落。太阳明媚的时候,两家的公鸡母鸡就跃上墙,站着的、卧着的、相互家长里短地聊着,偶尔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拉开一副要决斗的架势。她经常哭。先是她哭,接着是孩子们哭。墙太低了,抵挡不住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对于声音来说,简直如履平地。她的男人经常打她……”这里看似描写两个斗架的公鸡母鸡,实则是描写两个一直打架的人。描写那个丈夫是这样的:“她的男人看上去就凶巴巴的。喜欢皱眉头,动不动两条眉头就拧巴在一起,只要眉头一皱,两只细长眼角就像有人用细线把眉梢吊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顿时凶狠了很多,比《水浒传》里的李逵更李逵。”形象的比喻,让读者对这个人物增加了一种憎恶感、一种对女人的爱怜、对家暴的仇恨和声讨,以及激起一种反抗的力量。《年味系列》里“扫厦、煮油、蒸馍、备菜、贴对”这些土语的巧妙运用,使她的语言极具美感。这样的语言在文章里比比皆是,几乎成为每篇文章的亮点,也使她的散文读起来亲切,很有味道。这恐怕也是她的散文极具卖点的原因之一。
韵荷的散文名字叫《奔跑的村庄》,这固有的村庄已打破了多少年的沉静,也逐步开始喧嚣起来。乡村拖在城市的屁股后面,也在一路地朝前奔跑,跑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跑得不伦不类,跑成了个“四不像”。这是韵荷对家乡、对村庄、对父老乡亲的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她的认知世界里,觉得城市应该有城市的高楼和热闹,乡村就应该有乡村的碧绿和宁静,有它的个性、有它的气质、有它的生机勃勃,有它一切都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了她这个游子在急切地呼喊着!韵荷的散文集《奔跑的村庄》出版了,这是她继《遇见自己》后的第二本散文集。听说两本书在网上卖得挺好,我着实为她高兴。要知道如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抱着手机刷视频、玩游戏,很少对纸质书感兴趣,而韵荷的散文却很受欢迎,不由让人想走进她的书里探个究竟。
她的书名不虚传,打开就想起“开卷有益”那句话。她的书是引人入胜的、是有趣味的、是富含哲理的、是接地气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的。
她的书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韵荷的散文,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村庄,写的全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是张家大爷、李家奶奶,是你家大哥、邻家大姐,抑或是自家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表哥表姐及远亲近邻的父老乡亲们。
她和她的村庄,是无法割舍的。那是她的根据地,是流淌在她血液里浓浓的因子;是维系她生命里的那根长长的脐带;是她一辈子的灵魂栖息地。她用她的笔触为家乡代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用她的笔写出家乡在发展中的阵痛幽怨和父老乡亲的苦辣酸甜。
她的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一是每一个故事都很生动出彩。她的人物是鲜活的、立体的、独具特色的。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个一个镜头推出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画面感,让读者和人物瞬间融为一体,并带着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其痛痒。
其二是语言具有趣味性和区域代表性。拟人和拟物化的描写,加上典型的地方方言,让语言达到了一种至高至极的纯粹状态,充满了张力,让人物也活了起来,丰富而多彩。她的有些语言和人物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她写爸妈在土地上劳作:“黑褐色的土地被爸妈翻腾得起了‘浪花’,一犁接一犁,牛累得浑身直冒汗,土地乐得直翻滚。路边枝杈上的喜鹊不停地喊:‘歇一歇呗,歇一歇呗!’最懂我的,是那只穿着花衣服的喜鹊。那年,爸妈像是长在了桃园里、长在土地上;忙完了桃树,忙果树;忙完了果树,忙柿子树……”写她在这个桃园看桃时,“像是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哪个桃大摘哪个,哪个桃红吃哪个。吃饱了,躺在树杈间,抱着一怀凉风,闻着桃香,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武侠梦”。她写《菊花嫂子》时这样形容:“她拉着我的手,依然显得敦厚、朴素、实诚。她上嘴唇很厚,向外翻着,熟悉的大龅牙裸露在外,好敬业的哨兵啊!阳光热烈,花草含笑,我们咫尺而立,一股清风在我们之间穿行。”写到菊花嫂子的婆婆肥胖,用了“幅员辽阔”,走起路来“动静格外大”。她的这个语境和独特的比喻,让人物个性顿时活了起来,充分发挥了读者对人物的无限想象,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到菊花嫂子养了一儿一女,女娃长相随了父亲,模样俊俏,温柔娴静,儿子则像她母亲,相貌平平,老实木讷。这时的菊花嫂子眼里噙着泪花说:“让村人见笑了。”而这时的韵荷也笔锋一转,用乡间俚语这样描写:“在村子里,世世代代为邻,谁家锅底没点灰,谁顾得上笑话谁呀!”一句俚语的巧妙运用,让整篇文章有了灵魂,有了生命力。《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里,写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文学女人是她的邻居,“她家居前,我家居后,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土墙很薄、很低、也很脆。冬天,西北风呼啸而来,那墙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落。太阳明媚的时候,两家的公鸡母鸡就跃上墙,站着的、卧着的、相互家长里短地聊着,偶尔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拉开一副要决斗的架势。她经常哭。先是她哭,接着是孩子们哭。墙太低了,抵挡不住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对于声音来说,简直如履平地。她的男人经常打她……”这里看似描写两个斗架的公鸡母鸡,实则是描写两个一直打架的人。描写那个丈夫是这样的:“她的男人看上去就凶巴巴的。喜欢皱眉头,动不动两条眉头就拧巴在一起,只要眉头一皱,两只细长眼角就像有人用细线把眉梢吊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顿时凶狠了很多,比《水浒传》里的李逵更李逵。”形象的比喻,让读者对这个人物增加了一种憎恶感、一种对女人的爱怜、对家暴的仇恨和声讨,以及激起一种反抗的力量。《年味系列》里“扫厦、煮油、蒸馍、备菜、贴对”这些土语的巧妙运用,使她的语言极具美感。这样的语言在文章里比比皆是,几乎成为每篇文章的亮点,也使她的散文读起来亲切,很有味道。这恐怕也是她的散文极具卖点的原因之一。
韵荷的散文名字叫《奔跑的村庄》,这固有的村庄已打破了多少年的沉静,也逐步开始喧嚣起来。乡村拖在城市的屁股后面,也在一路地朝前奔跑,跑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跑得不伦不类,跑成了个“四不像”。这是韵荷对家乡、对村庄、对父老乡亲的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她的认知世界里,觉得城市应该有城市的高楼和热闹,乡村就应该有乡村的碧绿和宁静,有它的个性、有它的气质、有它的生机勃勃,有它一切都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了她这个游子在急切地呼喊着!韵荷的散文集《奔跑的村庄》出版了,这是她继《遇见自己》后的第二本散文集。听说两本书在网上卖得挺好,我着实为她高兴。要知道如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抱着手机刷视频、玩游戏,很少对纸质书感兴趣,而韵荷的散文却很受欢迎,不由让人想走进她的书里探个究竟。
她的书名不虚传,打开就想起“开卷有益”那句话。她的书是引人入胜的、是有趣味的、是富含哲理的、是接地气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的。
她的书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韵荷的散文,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村庄,写的全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是张家大爷、李家奶奶,是你家大哥、邻家大姐,抑或是自家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表哥表姐及远亲近邻的父老乡亲们。
她和她的村庄,是无法割舍的。那是她的根据地,是流淌在她血液里浓浓的因子;是维系她生命里的那根长长的脐带;是她一辈子的灵魂栖息地。她用她的笔触为家乡代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用她的笔写出家乡在发展中的阵痛幽怨和父老乡亲的苦辣酸甜。
她的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一是每一个故事都很生动出彩。她的人物是鲜活的、立体的、独具特色的。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个一个镜头推出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画面感,让读者和人物瞬间融为一体,并带着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其痛痒。
其二是语言具有趣味性和区域代表性。拟人和拟物化的描写,加上典型的地方方言,让语言达到了一种至高至极的纯粹状态,充满了张力,让人物也活了起来,丰富而多彩。她的有些语言和人物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她写爸妈在土地上劳作:“黑褐色的土地被爸妈翻腾得起了‘浪花’,一犁接一犁,牛累得浑身直冒汗,土地乐得直翻滚。路边枝杈上的喜鹊不停地喊:‘歇一歇呗,歇一歇呗!’最懂我的,是那只穿着花衣服的喜鹊。那年,爸妈像是长在了桃园里、长在土地上;忙完了桃树,忙果树;忙完了果树,忙柿子树……”写她在这个桃园看桃时,“像是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哪个桃大摘哪个,哪个桃红吃哪个。吃饱了,躺在树杈间,抱着一怀凉风,闻着桃香,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武侠梦”。她写《菊花嫂子》时这样形容:“她拉着我的手,依然显得敦厚、朴素、实诚。她上嘴唇很厚,向外翻着,熟悉的大龅牙裸露在外,好敬业的哨兵啊!阳光热烈,花草含笑,我们咫尺而立,一股清风在我们之间穿行。”写到菊花嫂子的婆婆肥胖,用了“幅员辽阔”,走起路来“动静格外大”。她的这个语境和独特的比喻,让人物个性顿时活了起来,充分发挥了读者对人物的无限想象,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到菊花嫂子养了一儿一女,女娃长相随了父亲,模样俊俏,温柔娴静,儿子则像她母亲,相貌平平,老实木讷。这时的菊花嫂子眼里噙着泪花说:“让村人见笑了。”而这时的韵荷也笔锋一转,用乡间俚语这样描写:“在村子里,世世代代为邻,谁家锅底没点灰,谁顾得上笑话谁呀!”一句俚语的巧妙运用,让整篇文章有了灵魂,有了生命力。《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里,写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文学女人是她的邻居,“她家居前,我家居后,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土墙很薄、很低、也很脆。冬天,西北风呼啸而来,那墙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落。太阳明媚的时候,两家的公鸡母鸡就跃上墙,站着的、卧着的、相互家长里短地聊着,偶尔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拉开一副要决斗的架势。她经常哭。先是她哭,接着是孩子们哭。墙太低了,抵挡不住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对于声音来说,简直如履平地。她的男人经常打她……”这里看似描写两个斗架的公鸡母鸡,实则是描写两个一直打架的人。描写那个丈夫是这样的:“她的男人看上去就凶巴巴的。喜欢皱眉头,动不动两条眉头就拧巴在一起,只要眉头一皱,两只细长眼角就像有人用细线把眉梢吊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顿时凶狠了很多,比《水浒传》里的李逵更李逵。”形象的比喻,让读者对这个人物增加了一种憎恶感、一种对女人的爱怜、对家暴的仇恨和声讨,以及激起一种反抗的力量。《年味系列》里“扫厦、煮油、蒸馍、备菜、贴对”这些土语的巧妙运用,使她的语言极具美感。这样的语言在文章里比比皆是,几乎成为每篇文章的亮点,也使她的散文读起来亲切,很有味道。这恐怕也是她的散文极具卖点的原因之一。
韵荷的散文名字叫《奔跑的村庄》,这固有的村庄已打破了多少年的沉静,也逐步开始喧嚣起来。乡村拖在城市的屁股后面,也在一路地朝前奔跑,跑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跑得不伦不类,跑成了个“四不像”。这是韵荷对家乡、对村庄、对父老乡亲的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她的认知世界里,觉得城市应该有城市的高楼和热闹,乡村就应该有乡村的碧绿和宁静,有它的个性、有它的气质、有它的生机勃勃,有它一切都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了她这个游子在急切地呼喊着!
私信、微信、打电话联系!
她的书名不虚传,打开就想起“开卷有益”那句话。她的书是引人入胜的、是有趣味的、是富含哲理的、是接地气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的。
她的书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韵荷的散文,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村庄,写的全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是张家大爷、李家奶奶,是你家大哥、邻家大姐,抑或是自家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表哥表姐及远亲近邻的父老乡亲们。
她和她的村庄,是无法割舍的。那是她的根据地,是流淌在她血液里浓浓的因子;是维系她生命里的那根长长的脐带;是她一辈子的灵魂栖息地。她用她的笔触为家乡代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用她的笔写出家乡在发展中的阵痛幽怨和父老乡亲的苦辣酸甜。
她的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一是每一个故事都很生动出彩。她的人物是鲜活的、立体的、独具特色的。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个一个镜头推出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画面感,让读者和人物瞬间融为一体,并带着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其痛痒。
其二是语言具有趣味性和区域代表性。拟人和拟物化的描写,加上典型的地方方言,让语言达到了一种至高至极的纯粹状态,充满了张力,让人物也活了起来,丰富而多彩。她的有些语言和人物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她写爸妈在土地上劳作:“黑褐色的土地被爸妈翻腾得起了‘浪花’,一犁接一犁,牛累得浑身直冒汗,土地乐得直翻滚。路边枝杈上的喜鹊不停地喊:‘歇一歇呗,歇一歇呗!’最懂我的,是那只穿着花衣服的喜鹊。那年,爸妈像是长在了桃园里、长在土地上;忙完了桃树,忙果树;忙完了果树,忙柿子树……”写她在这个桃园看桃时,“像是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哪个桃大摘哪个,哪个桃红吃哪个。吃饱了,躺在树杈间,抱着一怀凉风,闻着桃香,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武侠梦”。她写《菊花嫂子》时这样形容:“她拉着我的手,依然显得敦厚、朴素、实诚。她上嘴唇很厚,向外翻着,熟悉的大龅牙裸露在外,好敬业的哨兵啊!阳光热烈,花草含笑,我们咫尺而立,一股清风在我们之间穿行。”写到菊花嫂子的婆婆肥胖,用了“幅员辽阔”,走起路来“动静格外大”。她的这个语境和独特的比喻,让人物个性顿时活了起来,充分发挥了读者对人物的无限想象,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到菊花嫂子养了一儿一女,女娃长相随了父亲,模样俊俏,温柔娴静,儿子则像她母亲,相貌平平,老实木讷。这时的菊花嫂子眼里噙着泪花说:“让村人见笑了。”而这时的韵荷也笔锋一转,用乡间俚语这样描写:“在村子里,世世代代为邻,谁家锅底没点灰,谁顾得上笑话谁呀!”一句俚语的巧妙运用,让整篇文章有了灵魂,有了生命力。《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里,写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文学女人是她的邻居,“她家居前,我家居后,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土墙很薄、很低、也很脆。冬天,西北风呼啸而来,那墙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落。太阳明媚的时候,两家的公鸡母鸡就跃上墙,站着的、卧着的、相互家长里短地聊着,偶尔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拉开一副要决斗的架势。她经常哭。先是她哭,接着是孩子们哭。墙太低了,抵挡不住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对于声音来说,简直如履平地。她的男人经常打她……”这里看似描写两个斗架的公鸡母鸡,实则是描写两个一直打架的人。描写那个丈夫是这样的:“她的男人看上去就凶巴巴的。喜欢皱眉头,动不动两条眉头就拧巴在一起,只要眉头一皱,两只细长眼角就像有人用细线把眉梢吊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顿时凶狠了很多,比《水浒传》里的李逵更李逵。”形象的比喻,让读者对这个人物增加了一种憎恶感、一种对女人的爱怜、对家暴的仇恨和声讨,以及激起一种反抗的力量。《年味系列》里“扫厦、煮油、蒸馍、备菜、贴对”这些土语的巧妙运用,使她的语言极具美感。这样的语言在文章里比比皆是,几乎成为每篇文章的亮点,也使她的散文读起来亲切,很有味道。这恐怕也是她的散文极具卖点的原因之一。
韵荷的散文名字叫《奔跑的村庄》,这固有的村庄已打破了多少年的沉静,也逐步开始喧嚣起来。乡村拖在城市的屁股后面,也在一路地朝前奔跑,跑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跑得不伦不类,跑成了个“四不像”。这是韵荷对家乡、对村庄、对父老乡亲的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她的认知世界里,觉得城市应该有城市的高楼和热闹,乡村就应该有乡村的碧绿和宁静,有它的个性、有它的气质、有它的生机勃勃,有它一切都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了她这个游子在急切地呼喊着!韵荷的散文集《奔跑的村庄》出版了,这是她继《遇见自己》后的第二本散文集。听说两本书在网上卖得挺好,我着实为她高兴。要知道如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抱着手机刷视频、玩游戏,很少对纸质书感兴趣,而韵荷的散文却很受欢迎,不由让人想走进她的书里探个究竟。
她的书名不虚传,打开就想起“开卷有益”那句话。她的书是引人入胜的、是有趣味的、是富含哲理的、是接地气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的。
她的书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韵荷的散文,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村庄,写的全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是张家大爷、李家奶奶,是你家大哥、邻家大姐,抑或是自家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表哥表姐及远亲近邻的父老乡亲们。
她和她的村庄,是无法割舍的。那是她的根据地,是流淌在她血液里浓浓的因子;是维系她生命里的那根长长的脐带;是她一辈子的灵魂栖息地。她用她的笔触为家乡代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用她的笔写出家乡在发展中的阵痛幽怨和父老乡亲的苦辣酸甜。
她的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一是每一个故事都很生动出彩。她的人物是鲜活的、立体的、独具特色的。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个一个镜头推出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画面感,让读者和人物瞬间融为一体,并带着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其痛痒。
其二是语言具有趣味性和区域代表性。拟人和拟物化的描写,加上典型的地方方言,让语言达到了一种至高至极的纯粹状态,充满了张力,让人物也活了起来,丰富而多彩。她的有些语言和人物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她写爸妈在土地上劳作:“黑褐色的土地被爸妈翻腾得起了‘浪花’,一犁接一犁,牛累得浑身直冒汗,土地乐得直翻滚。路边枝杈上的喜鹊不停地喊:‘歇一歇呗,歇一歇呗!’最懂我的,是那只穿着花衣服的喜鹊。那年,爸妈像是长在了桃园里、长在土地上;忙完了桃树,忙果树;忙完了果树,忙柿子树……”写她在这个桃园看桃时,“像是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哪个桃大摘哪个,哪个桃红吃哪个。吃饱了,躺在树杈间,抱着一怀凉风,闻着桃香,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武侠梦”。她写《菊花嫂子》时这样形容:“她拉着我的手,依然显得敦厚、朴素、实诚。她上嘴唇很厚,向外翻着,熟悉的大龅牙裸露在外,好敬业的哨兵啊!阳光热烈,花草含笑,我们咫尺而立,一股清风在我们之间穿行。”写到菊花嫂子的婆婆肥胖,用了“幅员辽阔”,走起路来“动静格外大”。她的这个语境和独特的比喻,让人物个性顿时活了起来,充分发挥了读者对人物的无限想象,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到菊花嫂子养了一儿一女,女娃长相随了父亲,模样俊俏,温柔娴静,儿子则像她母亲,相貌平平,老实木讷。这时的菊花嫂子眼里噙着泪花说:“让村人见笑了。”而这时的韵荷也笔锋一转,用乡间俚语这样描写:“在村子里,世世代代为邻,谁家锅底没点灰,谁顾得上笑话谁呀!”一句俚语的巧妙运用,让整篇文章有了灵魂,有了生命力。《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里,写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文学女人是她的邻居,“她家居前,我家居后,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土墙很薄、很低、也很脆。冬天,西北风呼啸而来,那墙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落。太阳明媚的时候,两家的公鸡母鸡就跃上墙,站着的、卧着的、相互家长里短地聊着,偶尔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拉开一副要决斗的架势。她经常哭。先是她哭,接着是孩子们哭。墙太低了,抵挡不住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对于声音来说,简直如履平地。她的男人经常打她……”这里看似描写两个斗架的公鸡母鸡,实则是描写两个一直打架的人。描写那个丈夫是这样的:“她的男人看上去就凶巴巴的。喜欢皱眉头,动不动两条眉头就拧巴在一起,只要眉头一皱,两只细长眼角就像有人用细线把眉梢吊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顿时凶狠了很多,比《水浒传》里的李逵更李逵。”形象的比喻,让读者对这个人物增加了一种憎恶感、一种对女人的爱怜、对家暴的仇恨和声讨,以及激起一种反抗的力量。《年味系列》里“扫厦、煮油、蒸馍、备菜、贴对”这些土语的巧妙运用,使她的语言极具美感。这样的语言在文章里比比皆是,几乎成为每篇文章的亮点,也使她的散文读起来亲切,很有味道。这恐怕也是她的散文极具卖点的原因之一。
韵荷的散文名字叫《奔跑的村庄》,这固有的村庄已打破了多少年的沉静,也逐步开始喧嚣起来。乡村拖在城市的屁股后面,也在一路地朝前奔跑,跑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跑得不伦不类,跑成了个“四不像”。这是韵荷对家乡、对村庄、对父老乡亲的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她的认知世界里,觉得城市应该有城市的高楼和热闹,乡村就应该有乡村的碧绿和宁静,有它的个性、有它的气质、有它的生机勃勃,有它一切都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了她这个游子在急切地呼喊着!韵荷的散文集《奔跑的村庄》出版了,这是她继《遇见自己》后的第二本散文集。听说两本书在网上卖得挺好,我着实为她高兴。要知道如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抱着手机刷视频、玩游戏,很少对纸质书感兴趣,而韵荷的散文却很受欢迎,不由让人想走进她的书里探个究竟。
她的书名不虚传,打开就想起“开卷有益”那句话。她的书是引人入胜的、是有趣味的、是富含哲理的、是接地气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的。
她的书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韵荷的散文,几乎都围绕着她的村庄,写的全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是张家大爷、李家奶奶,是你家大哥、邻家大姐,抑或是自家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表哥表姐及远亲近邻的父老乡亲们。
她和她的村庄,是无法割舍的。那是她的根据地,是流淌在她血液里浓浓的因子;是维系她生命里的那根长长的脐带;是她一辈子的灵魂栖息地。她用她的笔触为家乡代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用她的笔写出家乡在发展中的阵痛幽怨和父老乡亲的苦辣酸甜。
她的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一是每一个故事都很生动出彩。她的人物是鲜活的、立体的、独具特色的。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个一个镜头推出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画面感,让读者和人物瞬间融为一体,并带着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其痛痒。
其二是语言具有趣味性和区域代表性。拟人和拟物化的描写,加上典型的地方方言,让语言达到了一种至高至极的纯粹状态,充满了张力,让人物也活了起来,丰富而多彩。她的有些语言和人物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她写爸妈在土地上劳作:“黑褐色的土地被爸妈翻腾得起了‘浪花’,一犁接一犁,牛累得浑身直冒汗,土地乐得直翻滚。路边枝杈上的喜鹊不停地喊:‘歇一歇呗,歇一歇呗!’最懂我的,是那只穿着花衣服的喜鹊。那年,爸妈像是长在了桃园里、长在土地上;忙完了桃树,忙果树;忙完了果树,忙柿子树……”写她在这个桃园看桃时,“像是孙悟空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哪个桃大摘哪个,哪个桃红吃哪个。吃饱了,躺在树杈间,抱着一怀凉风,闻着桃香,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武侠梦”。她写《菊花嫂子》时这样形容:“她拉着我的手,依然显得敦厚、朴素、实诚。她上嘴唇很厚,向外翻着,熟悉的大龅牙裸露在外,好敬业的哨兵啊!阳光热烈,花草含笑,我们咫尺而立,一股清风在我们之间穿行。”写到菊花嫂子的婆婆肥胖,用了“幅员辽阔”,走起路来“动静格外大”。她的这个语境和独特的比喻,让人物个性顿时活了起来,充分发挥了读者对人物的无限想象,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到菊花嫂子养了一儿一女,女娃长相随了父亲,模样俊俏,温柔娴静,儿子则像她母亲,相貌平平,老实木讷。这时的菊花嫂子眼里噙着泪花说:“让村人见笑了。”而这时的韵荷也笔锋一转,用乡间俚语这样描写:“在村子里,世世代代为邻,谁家锅底没点灰,谁顾得上笑话谁呀!”一句俚语的巧妙运用,让整篇文章有了灵魂,有了生命力。《文学,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里,写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文学女人是她的邻居,“她家居前,我家居后,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土墙很薄、很低、也很脆。冬天,西北风呼啸而来,那墙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落。太阳明媚的时候,两家的公鸡母鸡就跃上墙,站着的、卧着的、相互家长里短地聊着,偶尔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拉开一副要决斗的架势。她经常哭。先是她哭,接着是孩子们哭。墙太低了,抵挡不住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对于声音来说,简直如履平地。她的男人经常打她……”这里看似描写两个斗架的公鸡母鸡,实则是描写两个一直打架的人。描写那个丈夫是这样的:“她的男人看上去就凶巴巴的。喜欢皱眉头,动不动两条眉头就拧巴在一起,只要眉头一皱,两只细长眼角就像有人用细线把眉梢吊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顿时凶狠了很多,比《水浒传》里的李逵更李逵。”形象的比喻,让读者对这个人物增加了一种憎恶感、一种对女人的爱怜、对家暴的仇恨和声讨,以及激起一种反抗的力量。《年味系列》里“扫厦、煮油、蒸馍、备菜、贴对”这些土语的巧妙运用,使她的语言极具美感。这样的语言在文章里比比皆是,几乎成为每篇文章的亮点,也使她的散文读起来亲切,很有味道。这恐怕也是她的散文极具卖点的原因之一。
韵荷的散文名字叫《奔跑的村庄》,这固有的村庄已打破了多少年的沉静,也逐步开始喧嚣起来。乡村拖在城市的屁股后面,也在一路地朝前奔跑,跑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跑得不伦不类,跑成了个“四不像”。这是韵荷对家乡、对村庄、对父老乡亲的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她的认知世界里,觉得城市应该有城市的高楼和热闹,乡村就应该有乡村的碧绿和宁静,有它的个性、有它的气质、有它的生机勃勃,有它一切都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了她这个游子在急切地呼喊着!
私信、微信、打电话联系!
联系人
penguinzhuyun
私信、微信、打电话联系!
立即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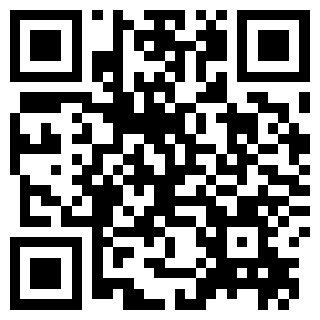
运城社区客户端
查看和发布更多信息。